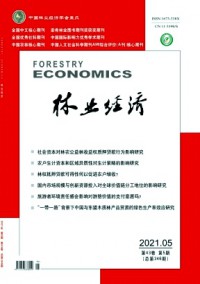關于父親的詩句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關于父親的詩句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關于父親的詩句范文第1篇
豐臺區勞動局:
你局《關于陳舊工傷的供養親屬撫恤金能否參照〈北京市企業職工工傷范圍和保險待遇暫行辦法〉執行的請示》收悉,現函復如下:
工傷職工的供養親屬撫恤標準,1978年前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的有關規定執行;1979年1月至1996年5月前按《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國發〔1978〕104號)的有關規定執行;1996年6月至1996年10月按《關于調整企業職工工傷保險待遇標準的通知》(京勞險發〔1996〕120號)規定執行;1996年10月至今按《北京市企業職工工傷范圍和保險待遇暫行辦法》(京勞險發〔1997〕228號)的規定執行。
關于父親的詩句范文第2篇
厚厚的一本書,裝幀精美,封面是海子親手畫的太陽與山岡,就像一個人伸出手。凸出的墨點,自有一股攝人的魔力。
我翻開書,細細地看。
原本以為自盡者都是可悲的厭世者,自從讀過梵高傳記《Just For Life》后,才改變了自己的看法。讀到海子的詩歌才明白這一觀點是如何的錯誤:“這個渴望飛翔的人注定要死于大地,但是誰又能肯定海子的死不是另一種意義的飛翔?擺脫漫漫長夜,根深蒂固的靈魂之苦,呼應天國彌賽亞洪亮的召喚。”這是西川的論說。
海子喜歡梵高,他不止一次給這位他的瘦哥哥(他稱梵高“瘦哥哥”)寫過詩歌。美術評論家休斯說:“梵高對這個世界的印象太過強烈,他只得消失。”我想,海子大約也是死于此。他們都是一樣的渴望生活。
第一首給予我強烈震撼的詩歌是《二月的雪,二月的雨》,荒涼大地上的天空,上卷下卷圣書,令人感覺就有如見證了一場重生,這種重生是荒蕪的,空曠的,不為人知曉的。那里有詩人靈魂混沌的融合以及一些遠方的歌聲。
還有那些描寫青海湖與的詩歌:“你在我指間化作雪白的飛鳥”,“沒有任何淚水使我變成花朵,沒有任何國王使我變成王座。”這些詩歌出乎尋常的清朗安靜。詩人不能沒有精神家園而寫出詩,海子一生都夢想遠方:“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盡管如此,他依然為遠方寫下無數美麗的詩句:“你從遠方來,我到遠方去/遙遠的路程經過這里/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安慰?”“我的酒杯上落滿灰塵/而遙遠的路程卻干干凈凈。”遠方是美麗的清澈的,春暖花開的,但海子也知道“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所有能夠到達的地方,都不能稱為遠方。遠方注定遼遠,海子筆下的青海湖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那天上勝景,是遙不可及的太陽城在塵世的化身。直到后來,海子也沒能從遠方中走出來。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個月,在一首十四行詩中他寫道:“遠方就是這樣,就是我站立的地方。”就像這樣,遠方可以幻滅,但永遠不能被抹去。
短詩中的“遠方”數不勝數,在他視之為生命的大詩《太陽·七部書》中,遠方的意象也比比皆是。《弒》與《你是父親的好女兒》簡直就是為遠方而寫。《弒》寫得是古巴比倫的詩歌競賽(完全詩人的臆想,無現實根據),關于兩個來自遠方的詩人青草與吉卜賽的詩劇。而《你是父親的好女兒》開頭便是:“西海還非常遙遠,是的,非常遙遠。遠方的那些雪兒也深得像海一樣。”
遠方本身就是一首詩。
長詩中依然貫穿了一個悲劇性的念頭:“遠方永遠無法到達。”這樣一種悲觀的詩意,伴隨著海子一起躺在了1989年3月26日山海關的鐵路上。
如今海子的遠方已經荒蕪了二十余年,我像一個孩子,無意窺探到了其中的一點。但是海子沒有老去,他如愿以償地成為了詩歌王子,和他所崇敬的詩人梵高(海子認為他就是詩人)、雪萊、葉賽寧、荷爾德林、韓波、愛倫·坡一起生活在原始力量的周圍,正如西川所說:“海子的死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
關于父親的詩句范文第3篇
與特車服務公司一中隊隊長李守義共事的時間雖然不是很長,但從他平日一絲不茍的工作態度中,我深深感受到,沒有榮譽和鮮花,我們仍舊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黨員。
李守義的工作時間是從每天早上6點鐘開始的,而結束的時間卻只有星星知道了。每天早上,在車場你都會看到一個身影穿梭于那些龐大的重型車輛之間,或是在蹲在地上檢查輪胎是否缺氣、或是鉆到車底檢查底盤是否漏油,14臺車輛全部檢查完畢往往要蹲下站起幾十次,這對于患有腰間盤脫出的中年人來說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每次檢查完畢他都是累的直不起腰。不記得是誰說過,簡單的工作能夠千百次的重復去做 ,而每次都做得最好是最不簡單的。而這項簡單的工作他每天都是這樣重復著,不管刮風下雨,不管嚴寒酷暑,他從未間斷過。
李守義常對員工們說能自己修的咱們不找別人修,節約要從點滴做起。單位的車出現個什么小毛病,他從來都是帶領大家自己修理。一次,車隊唯一的一臺清蠟車發生了故障,這就意味著采油廠將無法熱洗,耽誤一系列的工作進程不說原油產量也將受到嚴重影響。趕緊把車修好投入生產是當務之急。而到修理廠修車的費用之高又會影響到成本支出。如何又能盡快的把車修好,又不耽誤甲方生產呢?他當機立斷,帶領車上的司機和泵工自己動手修理這臺車。經過查找原因是泵不上水,要進行扒泵處理。在扒泵過程中泵里的余壓將混著原油的污水噴射到大家的身上、臉上他們全然不顧,終于泵被修好了,而這平日里需要兩小時的工作兩他們只用了一個小時就完成了,不僅節余了成本,而且及時投入到了采油廠的熱洗工作,并沒有因為清蠟車的故障而耽誤熱洗任務,同時也受到了甲方的高度贊揚。象這樣小修小檢的工作對于一隊來說已是家常便飯,有的司機還調侃著說:“我們這些司機修車的技術都要比開車的技術高了!”
盡管特車服務公司是二線,可是司機的工作時間卻非常不規律,隨時有任務隨時出發、時刻保證甲方生產是他們雷達不動的工作標準。但是由于活多人少,加班就成了常事兒,有的時候在井場一干就是五六個小時,無法正常回家吃飯。為了保證工人們能夠正常工作,每次到了用餐時間他都主動給工人們送去可口的飯菜,而他自己卻總是為此錯過了吃飯的時間。用“一個蘿卜一個坑”這句話來形容一隊的人手是最恰當不過的了。要是哪個工人家中有點事情不能上班,車輛就無法派出。所以,每次遇到職工請假,他都主動承擔起出車的任務。
雖然車隊不是連續性生產單位,但只要一線不休息,車隊的車就甭想休息,時刻處于待命狀態。無論是“五·一”、國慶,還是元旦、春節,他都從未休過一天假。每年春天正是生產單位上產的黃金季節,為了保證甲方生產不受影響,十幾臺車每天都是滿復合運轉。而就在這最忙的節骨眼兒上,在興隆臺的父親卻患上了嚴重疾病,需要馬上動手術。聽到電話那頭父親帶著病痛
關于父親的詩句范文第4篇
曾經劍拔弩張的雙方終于坐到了談判桌前。談判的結果,就是陳寶成家和鄰居家“每一戶村民的利益訴求均得到了滿足”。
2014年11月24日這天,對方的承諾“全部到位”后,陳寶成家的房子被拆掉。第二天,他踏上了返回北京的旅途。途中,陳寶成通過一條微信與過去告別:“我們感謝大家,感謝對手,感謝世界!”
“故鄉從此是他鄉”
一身風骨立殘陽,
亦傲冰雪亦傲霜。
健筆凌云多偶得,
鐵肩道義少擔當。
誰人徒念關山近?
我輩終知返路長。
一葉浮萍歸大海,
男兒從此不還鄉。
在祖宅交付拆遷的2014年11月24日這天,陳寶成在微博上發表了這首詩。在另一則微博中,他寫下了“故鄉從此是他鄉”的詩句。
與羅大佑膾炙人口的歌曲《鹿港小鎮》中“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聽說他們挖走了家鄉的紅磚,砌上了水泥墻”等歌詞相比,陳寶成的詩句更顯蒼涼。
金溝子村,就是陳寶成的“鹿港小鎮”。
陳寶成的心情,他的摯友王進文和朱孝頂讀得懂。
在陳寶成的平度同鄉、有抗拆遷經歷的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王進文看來,陳寶成長達7年的抗爭,“既是出于陳寶成對中國法治的信仰,也是他對于300年聚族而居的鄉村生活的眷戀”。因為“這片土地上有他的父老鄉親,有他的童年記憶,更有他的始祖先人”。
2013年8月27日,自陳寶成被警方帶走后一直堅守在金溝子村的朱孝頂寫下了《平度案:家鄉家園與根——陳寶成案述評》一文。
和陳寶成一樣,朱孝頂也生長在鄉村。在深度介入陳寶成案之前,這位年輕人因痛失父親和岳父兩位老人而對家鄉和家園有了更深的理解:“家鄉與家園,是我們永遠扔不掉的奶瓶與童謠……家永遠是心底無法忘卻的港灣。”
作為一名專業從事征地與拆遷律師業務的律師,朱孝頂因為不得不面對城鎮化大潮吞噬故國與家園的現實,而常常對羅大佑的《鹿港小鎮》產生共鳴。
因為常年為失地者維權,朱孝頂禁不住發出這樣的追問:“被上樓”的農民,沒有了世世代代耕種的田地,沒有了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的農具和農活,誰來保障他們長遠的生計?
未站在“官方”一邊的司法個案
2015年5月1日,修改后的《行政訴訟法》將施行。按照參與這部法律修改工作的王才亮的預測,隨著這部法律的實施,征地與拆遷糾紛將大量涌進法院。
如何應對由此帶來的案件“井噴”,對各地法院將是一次大考。根據王才亮的觀察,為應對即將到來的“大考”,一些司法機關已經用個案交出了漂亮的案卷。平度拆遷系列案件就是其中一例。
按照《2014:中國拆遷年度報告》的描述,在青島檢方采納律師關于對陳寶成案不起訴的建議對陳寶成等人作出不起訴決定的同時,當地有關部門正在對“3·21縱火案”的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責任并已對行政機關有關責任人員進行問責。
同樣是在為平度拆遷系列案件爭得良好處理結果的2014年,王才亮領銜的專業從事征地拆遷法律服務的北京市才良律師事務所所案件的“勝訴比例在上升”。在南方的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撤銷了為公眾熟知的廣東朱惠來父子抗拆致死致傷多人案件的死刑判決將案件發回重審的同時,在拆遷矛盾比較突出的東北三省,一些老大難案件的原告也獲得勝訴。
如果更多執法者能讀懂被拆遷者的“故鄉情懷”,在下判決時把征地的官方和被拆遷的民眾作為“平等的訴訟主體”,更多陳寶成式的個案將會出現。
關于父親的詩句范文第5篇
在自己的家中感受不到溫暖和愛的柯勒律治羨慕的不僅是這對兄妹之間的親情,更多的是這對兄妹在詩歌創作上的默契與合力,更準確些說,是多蘿茜對詩人兄長的助力。
失去與尋找
多蘿茜有兩個哥哥,理查德和威廉,兩個弟弟,約翰與克里斯托弗。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英國湖區考克茅斯鎮上最好的房子是她與兄弟們短暫美好童年的見證。當律師的父親與富商女兒的母親給他們提供了優裕的成長環境。
作為家中唯一的女孩,她不僅受父母寵愛,還得到了兄弟們的愛護。若非家庭變故,這位中產階級的女孩兒本可以一直過著公主一樣的生活直到長大嫁人。她或許也會如簡奧斯丁一樣,以針線活為遮掩,書寫自己的小說、散文和詩歌。但對于多蘿茜而言,在短暫的幸福童年之后,在她與哥哥重聚之前,十幾年的時間里都活在這些悲劇與淚水中。
6歲時,母親病逝,家中無一女眷,父親把多蘿茜送到姨媽家。然而這一別,直到五年后父親病逝,她也再沒回過家中。父親走后,他所服務的羅德老爺不歸還欠發工資的不義行動讓這幾個孩子不僅失去了父母雙親這片天,而且也失去了獲得任何遺產(包括房子)的可能。
多蘿茜和兄弟們很長一段時間無家可歸。1794年,還未滿23歲的多蘿茜從親戚家奔向已經從劍橋大學畢業的兄長威廉,他們在湖區、多賽特郡等地漂泊。經濟來源多是兄長朋友的資助。他們不停地在尋找家園,又不停地失去家園。成年后的兄妹在不斷尋找一個能將他們帶回到失去的家園、補償失去父母之痛的地方。
威廉想成為一名詩人,與舅舅對他投身宗教的期望完全相反,除了夢想,他一無所有。多蘿茜在哥哥身邊,鼓勵他,批評他,他是華茲華斯的作品最早最客觀的評論者之一。她與他一起守護著他的詩人夢想,一起尋找與修復華茲華斯在變質的法國大革命中受重創的理想與心。
多蘿西曾經在與好友簡波拉德的書信中說威廉具備她其他幾個兄弟所共有的所有美德,即堅持、真誠,然而最吸引她的是威廉在所喜愛的事物面前所自然流露出的那種愛的力度,他對事物的一種“不安的警覺性”,一種永不褪去的柔情,還有說話、做事時的謹慎。
而華茲華斯在他著名的自傳長詩《序曲》回溯妹妹在自己迷茫歲月中的作用時,這樣說:“是她/使我保持了與真實自我的聯絡,/因此將我拯救。”(丁宏為譯)在某種程度上來講,創作也是兄妹兩人重建家園的努力之一。
華茲華斯喜歡他這位唯一的妹妹在詩歌閱讀上的品味與鑒賞能力,他欣賞并且羨慕她所具有的異常敏感的詩人一般的眼睛與耳朵。他在妹妹這里得到的不僅僅是創作的靈感,更多的是一種讓他堅持做詩人的力量,是一份讓他不畏外在世界與言論的安心。
他另一詩作《埃斯威特山谷》(The Vale of Esthwaite),一首國內讀者鮮少讀到的詩中曾經這樣寫多蘿茜:“我愛著的妹妹/她深深溫暖了一位兄長的心。”
這對在苦難中團聚的兄妹最終在詩作、在湖區格拉斯米爾的安穩中慢慢擦干童年的眼淚。有心的讀者可以在他們的作品中尋得淡淡的淚痕。
“她給我一雙耳朵,一雙眼”
多蘿茜對自然萬物的敏感,細縝的觀察力得到了她的詩人兄長以及他們共同的好友柯勒律治的贊美。他們在英國南部時經常三個人一起散步,一起討論。多蘿茜說他們是三個身體,一個靈魂。他們三個友誼的巔峰也是兩位偉大浪漫主義詩人創作的巔峰時期。
多蘿茜寫日志,兩個大詩人閱讀。多蘿茜初始記錄日志時并未想著出版,她最初寫只是為了“給威廉一些樂子”。而多蘿茜沒有想到的是,無論對于華茲華斯還是對柯勒律治,這漸漸成了他們創作的靈感來源。
讀者所熟悉的《詠水仙》中有這樣的詩句:“驀然舉目,我望見一叢/金黃的水仙,繽紛茂密;/在湖水之濱,樹蔭之下,/正隨風搖曳,舞姿瀟灑……搖顫著(tossing)花冠,輕盈飄舞(dance)。/湖面的漣漪也迎風起舞,/水仙的歡悅卻勝似漣漪;有了這樣愉快的伴侶,/詩人怎能不心曠神怡(gay)!”(楊德豫 譯)華茲華斯早年的《夜景》(A Night-piece)與多蘿西在英國南部的日志《埃爾福克斯頓日志》中的記載一一呼應。他的《孤獨割麥女》也是c妹妹的《蘇格蘭游記日志》中的記載呼應。
很多時候真分不清是妹妹參考了哥哥,還是哥哥參考了妹妹。然而,這些或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兩位心靈都是詩心,所以才可以如此默契與相通。
華茲華斯的詩歌與妹妹的日志似乎成了彼此的注腳。一個是散文化的詩,一個是詩化的散文。華茲華斯在很多場合下表示過他對多蘿茜在自然中的觀察與回應之敏感與細致的羨慕之情。他在《麻雀窩》中寫她還是“口齒不清的小姑娘”時,對鳥窩的“又想接近它,又怕驚動它”的“好心腸”。(楊德豫譯)兩人在追蝴蝶時,她“生怕碰掉/蝶翅上面的薄粉”。(楊德豫譯)《麻雀窩》中準確地概述了她這位妹妹之于他的意義:
我后來的福分,早在童年
便已經與我同在;
她給我一雙耳朵,一雙眼,
銳敏的憂懼,瑣細的掛牽,
一顆心――甜蜜淚水的泉源,
思想,歡樂,還有愛。(楊德豫譯)
多蘿茜不僅是哥哥創作靈感的來源,在她中年生病之前的二十幾年的歲月里,她還是哥哥詩作的謄寫員。多蘿茜不僅謄寫,她有自己獨特的觀點,而她的觀點,華茲華斯幾乎在每次的修改中都采用。
多蘿茜是華茲華斯詩歌中“親愛的,親愛的妹妹“,是他詩中的“艾米莉”,是他筆下的 “愛瑪”,或許還是眾多學者與讀者莫衷一是的“露西”。他長達60余年的創作生涯中,這位妹妹無處不在。她與哥哥威廉一起旅行,一起安居格拉斯米爾,一起在創作中尋找過去、現在與明天。
生死不渝
多蘿茜將一生奉獻給了哥哥以及哥哥的孩子,一生未嫁。
關于多蘿茜的感情,文學界有些猜測,其實這些文學八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多蘿茜沒有致力于任何一種自己成家的可能,而是全身心地待在哥哥身邊。她照料他的生活,為他謄寫詩作,與他一起讀詩,為他讀詩,兄妹兩人給彼此溫暖,漸漸重建一個他們心目中的家。
如華茲華斯在詩中所言,他們幾個孤獨地抱在一起,一起面對這無依無靠的世界。華茲華斯也在書信中曾經寫過,每失去一個家人,他們余下的人會抱得更近,那是對失去的恐懼,那是對尚存的珍惜。沒有經受過這種切膚之痛的生離死別人,是難以體會他們這么緊的擁抱,這么親的共存的。
1831年她患精神動脈硬化癱瘓后,神智時常混亂,她在輪椅上度過了余生的24年,守著終年不滅的火爐。即使是夏天,她也不允熏壁爐里的火滅掉,神智清醒或不清的她守著那團火,守著那團年輕時的吉普賽女郎式的熱情,守著那實實在在的溫暖。她常常吟誦哥哥寫給她的詩,當她還是他眼中“小多蘿茜”的時候。
有人說多蘿茜的位置如此重要,華茲華斯對自己的妻子其實沒什么感情。這也是無稽之談。華茲華斯與妻子自幼年便相識,她與多蘿茜也是好朋友。兩人近半個世紀的婚姻中(1802-1850)始終恩愛不移。他們多年如一日充滿濃情蜜意的書信驚煞了所有讀者的心。瑪麗也并不是沒有文化的村婦,她的意見與多蘿茜的意見一樣被華茲華斯接受和重視。還是那首我們最熟悉的《詠水仙》。那首詩中華茲華斯認為最好的兩句:“水仙呵,便在心目中閃爍――/那是我孤寂時分的樂園”(楊德豫譯)便是出自妻子瑪麗之后。瑪麗與她的小姑子同一個屋檐下相處半個世紀之久,兩人未曾吵過一句。瑪麗在1850年送走了丈夫,在1855年送走了小姑多蘿茜,1859年在89歲時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