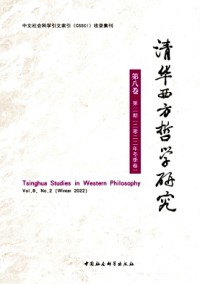西方文化概論筆記整理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西方文化概論筆記整理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西方文化概論筆記整理范文第1篇
【關鍵詞】巫蠱信仰;巫蠱功能;巫蠱規則;另類規范
【作者】陳寒非,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北京,100070
【中圖分類號】B9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4X(2015)03-0078-012
THE WITCHCRAFT, BELIEF AND THE FORMATION OF ORDER:
A Survey to the Phenomenon of “Witchcraft Infection” in M
Township in Xiangxi Autonomous Prefecture
Chen Hanfei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witchcraft beliefs, functions, and rules as well as other issues of the phenomenon of “witchcraft infection” in M township, Xiangx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t is found from fieldwork and case studies that witchcraft belief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confidant in heart, constituting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of witchcraft culture Witchcraft plays function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relying on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witchcraft belief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specific rules of witchcraft on the other The witchcraft rules are in line with the features of “alternative rules”, which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typical “alternative rules” The “alternative rules” play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to form and maintain social order in the local “little tradition”
Key Words: witchcraft beliefs; witchcraft function; witchcraft rules; alternative rules
以往關于巫術問題的研究往往從法律史的角度展開,古代司法審判與巫術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巫術儀式作為一項重要的司法儀式應用于神明裁判的場合。法律對巫術的制約作用也是不少學者討論的焦點,歷代統治者以法律的方式明確制裁巫術在社會生活中的應用,
從漢武帝時期的“巫蠱之亂”,到《唐律疏議》《宋刑統》《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古代法律文獻中關于巫術的禁止性規定,再到《名公書判清明集》等歷代判例判牘中關于巫術的處罰案例,巫術一直被統治者視為邪術,是國家法律懲戒的對象。相關研究可參見:武乾中國古代對巫術的法律懲禁[J]法學,1999(9)
盡管這種禁止在實踐中收效并不明顯。在面對當今社會中的巫術問題時,法學研究者們大多將其視為與法律相互抵牾的存在(巫術是落后社會文化的表現),尤其是持嚴格法教義學立場的學者們,對此更是持有排斥態度。隨著作為交叉法學的法律人類學的興起,巫術問題才逐步引起一些持有社科法學研究立場的學者們注意。
然而,在法律人類學的研究視野中,一直以來重點討論的問題是法律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民事及刑事法律的概念、權利義務體系以及具體適用過程,具體涉及的問題主要包括通過深描(Deep-description)處理的法律民族志寫作、法律多元主義(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與融合)、文化比較與法律文化闡釋、本土資源與法治語境化問題等,先后形成的理論及方法主要包括進化論理論、文化傳播理論、結構―功能主義理論以及闡釋人類學理論等。值得注意的是,盡管19世紀中期以來不少人類學家曾系統探討巫術與宗教問題,但是法律人類學在討論初民社會的“法”概念、法律進化形式、法律體系類型、互惠合作、糾紛解決等問題時,往往將巫術置入功能主義話語體系中,將其與法律、宗教、經濟等社會系統的功能進行橫向比較研究,而沒有充分注意到巫術與社會秩序之間的內在關聯。
本文的討論正是從法律人類學角度對上述問題的再度思考,重點剖析巫術與社會秩序形成之間的關系,透視這種關系賴以存在的文化基礎,這正是我們在今天討論法治時應該予以重視的問題。與此同時,本文的討論也試圖通過個案研究的方式回應當前法教義學在解釋某些具體法律現象時的不足,試圖在此基礎上區分兩者之間的功能差異及超越與互補關系。
2001年,蘇力教授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中國法學格局進行了考察,認為中國法學的發展存在三種范式,即政法法學、詮釋法學以及社科法學。時至今日,中國法學界(尤其是年輕學者群體)大體形成了法教義學與社科法學兩種主要研究范式的分野。2014年5月31日,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舉辦了“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對話”學術研討會,會上不少學者就兩種范式之間的關系、地位及功能等問題展開激烈討論。從這些討論內容來看,學者們大多都是從理論建構的角度展開,很少涉及對具體法律現象的分析。筆者認為,當前法教義學與社科法學各自除了在理論層面進行建構之外,還應該從具體的問題入手,在對具體法律現象的分析中總結概括出各自的功能及適用范圍。會議內容可參見《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對話會議論文集》以及會議綜述。
一、鄰里糾紛案引出的“中蠱”
本文研究的緣起是我于2013年7月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縣M鄉下關寨考察鄉村人民法庭的基本運作情況時,偶然中發現的一個案例。為了獲取第一手的調查資料,我參加了幾起案件的庭審(包括調解),并對人民法庭庭審的基本過程作了詳細的記錄。2013年7月14日的上午,我現場觀摩了一起鄰里糾紛案件的庭審經過,該案的基本案情如下:
M鄉下關寨村民李先起(原告)認為鄰居李永輝(被告)在修建房屋砌圍墻時擋住了自家門前的道路,妨礙了自己的正常通行。而李永輝并不同意李先起的說法。他認為,自己在修建圍墻時還留了很大一片地方,完全可從旁邊經過,而不存在侵占了李先起通行的道路。 雙方很快發生爭吵并動起手來,李先起阻止李永輝繼續砌墻,于是雙方到M鄉人民法庭進行調解解決。法庭經過調解,并沒有使雙方意見達成一致,甚至一度形成了僵局。無奈法官只好暫時停止調解工作,想在做雙方工作之后再進行調解。在這次調解快要結束之時,陳先起十分氣憤地向被告表示,“你等著,我讓先菊放蠱給你家,讓你全家死絕”。李永輝一聽到此話就表現出了極為驚恐的神色,仿佛如臨大敵一般。接下來的庭審出乎意外的順利,李永輝主動妥協,同意拆除已修了一半的圍墻。 參見調研筆記(編號201307―01)。
如果依照現有法教義學的立場,本案的案情比較簡單,也無特別復雜的概念術語或法律規則需要加以解釋和推理。然而,如果我們對該案進一步審視,至少能發現三個值得關注的疑點:第一,為何庭審開始之初雙方分歧較大,而后來卻突然發生了逆轉,雙方似乎很快形成了共識?第二,本案原告在庭審快要結束時所說的“你等著,我讓先菊放蠱給你家,讓你全家死絕”一語究竟起到何種作用,有著怎樣深刻內涵,屬于什么性質?第三,本案原告所提到的“先菊”是誰(具有何種身份),與原告存在何種關系,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本案的處理結果?針對這些疑問,我進一步挖掘與本案相關的材料。通過采訪李先起、李永輝以及M鄉下關寨的其他村民,我對李先菊和她的身份有了初步的了解。在訪談的過程中,M鄉下關寨村民是通過一個個具體的案例向我描述李先菊的,其中提到最多的是兩年前下關寨村民李國斌“中蠱”事件,事件基本經過如下:
2011年5月的一天中午,村民李國斌在干完農活回家后突然感覺肚子絞痛、惡心、頭痛。其母感到很詫異,因為他上午在地里干農活時一切正常,身體突然出現這種情況,且休息一會之后也不見好轉,反而表現得更為嚴重。于是,李母從里屋端來一碗生黃豆放在李國斌面前,沒想到他抓起一把黃豆就往口里塞,而且嚼得津津有味。這讓李母更加堅信了自己之前的判斷,兒子李國斌“中蠱”了。既然“中蠱”了,就得找到“解蠱”的方法,而解蠱方法的獲得必須得找到“放蠱”之人以及病人中的是何種類型的“蠱”。在李母的一番詢問之后,李永輝回憶,前幾天經過村里一戶人家的門口時,與正在門口洗菜的女主人聊了幾句,并大致描述了那個女人的年齡和相貌。李母一下緊張起來,根據兒子的描述,那個女人正是村里的“草鬼婆”李先菊。既然找出了(草鬼婆),就應該開始解蠱。于是,李母首先用刀剁砧板,在村里走了兩圈,口中還不斷地吆喝。但是,這個方法并不奏效,李永輝在家中疼得更加厲害。當天傍晚,李母又請來村里專門解蠱的“仙娘”,為李永輝解蠱。“仙娘”在李永輝睡覺的枕頭底下放下一個生雞蛋,過兩個小時之后取出。取出雞蛋之后打開,根據蛋黃的形狀最后判斷李永輝是中了“蜈蚣蠱”。隨后,“仙娘”用一碗水,取出黃紙,用火燒化在水中讓李永輝服下。但是,李永輝并未見好轉,而是更為嚴重。“仙娘”解釋,李國斌此時中蠱毒已深,已經無法治愈。李永輝在家熬了三日后,最終死亡。參見訪談錄音整理稿(編號2013071401)。
根據村民對“中蠱事件”的描述,我們不難看出,李先菊的身份是“草鬼婆”,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蠱婆”。在村民眼中,這是一種專門以放蠱為業的人,職業本身極具有負面的道德評價(我在后文中還將繼續分析“草鬼婆”身份以及李先菊本人)。在接下來的訪談中,村民李正德還為我講述了李先菊與李先起之間的關系:
李先起和李先菊是兩姐弟。李先菊早年嫁到離我們這里不遠的王公村,并且在那邊生了兩個孩子。唉,這個女人的命也是蠻不走好的。當時她生孩子的時候擺酒,我還過去幫忙做桌席了的。沒想到沒過幾年,她的兩個孩子先后得病夭折了,丈夫也得了肺癌去世了。她沒有地方去,只好又回到了娘家,到我們村寨里。她家老人去世后,她就一直住在祖屋里。
李先起是老弟,平時對他這個苦命的大姐也是很照顧的。
直到這個時候,我才明白,為什么在最初的鄰里糾紛調解案中李先起會提到李先菊。
細細推敲起來,其緣由可能有兩點:第一,李先菊的身份是“蠱婆”,在村人眼中是一個極具有神秘性的身份,而且帶著一些恐懼色彩(從中蠱事件中可以見到村民的態度);第二,李先起和李先菊是姐弟關系,血緣關系的存在使得他在談話的過程中刻意地提到李先菊,并作為自己重要的支援性力量。毫無疑問,雖然李先菊沒有直接參與庭審調解,但她始終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既然如此,為何李先起在庭審中會以“李先菊”為支援性力量?李先菊的“蠱婆”身份對于當地村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巫蠱在多大程度上推動/抑制當地秩序的形成?接下來的討論將圍繞這三個問題展開。
二、“蠱婆”身份的形成
在庭審過程中,對于原告李先起而言,李先菊顯然是作為一種對有利的支援性力量而存在。在對李先菊作為一種支援性力量存在的原因進行討論之前,我們首先需要討論李先菊“蠱婆”身份的產生或形成過程。換言之,李先菊究竟具有何種獨特之處,以至于在村民的心目中獲得這樣一種地位,而不管這種地位產生的基礎是源自正面或負面的評價。既然李先菊的身份是“蠱婆”,“蠱”可能是與之密切相關的。因此,要繼續討論這個問題,還得從“蠱”說起。
殷墟甲骨文中已經有“蠱”字,從甲骨象形來看,“蠱”是指“置百蟲于器皿之中”。除此之外,傳世典籍中對此也有詳細的描述。《隋書?地理志》講制蠱之法云:“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種存者留之, 蛇則曰蛇蠱,虱則曰虱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李時珍所著《本草綱目》“蟲四部”集解引唐代陳藏器原話云:“……取百蟲入甕中,經年開之,必有一蟲盡食諸蟲,即此名為蠱。”宋代鄭樵《通志》云:“造蠱之法,以百蟲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為蠱。”可見,“蠱”應該是指一種毒蟲。而“巫蠱”則是指通過巫師的活動以咒語之術喚來蠱蟲以害人之事。[1]5因此,“巫蠱”在歷史上一直被認為是邪術,成為統治者禁止的對象。[2]121-122在晚近的研究中,“巫蠱”也被認為是一種與意識形態有關的迷信而不被研究者們所重視,甚至將其視為。直到人類學整體論和文化相對論的進入,才逐漸將其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事象,這也是本文在討論過程中所堅持的基本立場。從“蠱”的定義以及歷史上針對“巫蠱”的態度,我們大致可以得出結論:“蠱”及“巫蠱”代表這一種負面的評價。
那么,李先菊為何與作為負面評價的“蠱”關聯起來了呢?在越軌社會學中,一旦某個社會主體的行為違反某個群體或社會的重要規范,那么這就是“社會越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蠱婆”也往往被某個共同體的集體意識評價為“異類”,屬于不被大多數成員接受的人。從更多的人類學田野調查資料來看,被認定為“蠱婆”的人往往在心理上、生理上或者家庭關系上都存在一些異同。
根據一些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許多社群都會對群體中的“異類”有特定的稱謂或區別對待。例如,云南蘭坪維西的那馬人將村中心事歹毒的女人稱之為“活人鬼”;怒江白族將經常在人背后說壞話的這類人稱之為“武惡鬼”;西雙版納自治州傣族將社群中長得較為漂亮的女性稱之為“琵琶鬼”;等等。參見呂大吉,何耀華,張公謹,等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傣族卷?哈尼族卷?景頗族卷?孟―高棉語族群體卷?普米族卷?珞巴族卷?阿昌族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呂大吉,何耀華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彝族卷?白族卷?基諾族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420―425
比如,長相上存在著某種缺陷,有眼疾(眼睛長期紅腫,眼屎較多等)、腿疾、無鼻或豁嘴等。再如,家庭遭遇較大的不幸,可能丈夫不幸去世,又可能小孩不幸夭折等。除了長相或生理上的缺陷,還有一種正好相反的現象是,被認定為“蠱婆”的人也可能在長相上太過于美麗。然而,無論是太過于美麗或者太過于丑陋,其背后都蘊含著一種重要的邏輯,即被認定為“蠱婆”的人都是某個社群中的“異類”,內外特征方面并不符合普通大眾一般性的審美或價值評判標準。[3]13這也就使得社區集體意識將其作為一種限制的對象,刻意從社群中將其排除或區別對待。如果上述人類學田野調查的證據成立的話,那么,李先菊正是屬于這種“異類”,這種“異”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首先,家庭及個人命運上的“異”。李先菊的家庭遭遇到巨大的變故。村民李正德在講述李先菊與李先起之間的關系時提到,“李先菊在嫁到鄰村王公村之后,兩個小孩和丈夫先后去世,沒有地方可去,只好又回到了娘家”。這在當地村民們看來,李先菊人生中的悲慘遭遇,一定是由于她前世做了很多孽,而在這輩子受到懲罰和報應,以至于命太剛強而將家里人克死(村民李正德語)。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因果報應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和表現形式,是嚴格恪守的信條,深深植根于人們的思想觀念之中。《周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書》云:“天道福善、禍。”《太平經》云:“善自命長,惡自命短。”佛教自東漢明帝傳入中原之后,進一步發展了因果報應觀念。東晉慧遠《三報論》云:“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后報。現報者,善惡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后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宋代以后,因果報應觀念經過理學的加工,直接要求人們身體力行,為國家正統文化所認同。
關于“報”的研究可參見楊聯報――中國社會關系的一個基礎[A]段昌國,等,譯//楊聯中國文化中“報”“保”“包”之意義:附錄二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65―98;霍存福復仇、報復刑、報應說[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5;徐昕通過私力救濟實現正義――兼論報應正義[J]法學評論,2003(5);王月清中國佛教善惡報應論初探[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1998(1),等等。
因此,村民們大多數認為李先菊的悲慘命運并無可值得同情之處,而是對前世罪惡的現世償還。李先菊的家庭遭遇使得她一直無法被村人接受,也無法融入到村莊共同體公共生活之中。
其次,經濟上的“異”。李先菊孤苦無依,家境十分貧困,在M村的經濟生活水平遠低于其他村民,而他的弟弟李先起在經濟上對她也無太多的幫助。正是由于這一因素,當地村民將其視為村莊人際關系網絡中的“另類”,一般情況下很少有人愿意與之人情來往,即使是正常的交往也比較少。馬林諾夫斯基對美拉尼西亞西北部的田野調查表明,“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的對稱性滲入到土著居民的生活之中,并作為一種法律約束力形式而存在”,具有“維護雙向服務的連續性和恰當性方面的社會功能”;因此,“結構的對稱性是互惠義務必不可少的基礎”。[4]13-15閻云翔對黑龍江下岬村禮物流動規則的研究,村莊中的人情往來規則是以“互惠”為基礎的,“它的實質――互惠原則――仍得以保存,并繼續作為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基本原則而起作用。”[5]122由此可見,互惠對于人際交往關系網絡的建立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互惠本身具有的經濟交換功能決定了互惠雙方存在一定的經濟或社會基礎。李先菊由于在村寨中十分貧困,又無兒女及其他親屬,無法為互惠提供經濟交換基礎,以至于村民基本上不與之往來,久而久之自然也就被排除在村莊人際交往網絡之外。作為對這種人際交往排除規則的現實反映,當地產生一整套關于人際交往的禁忌,其中就有“絕對不能接受蠱婆饋贈的食物,否則就會中蠱”(村民李正德語)。
最后,外貌上的“異”。根據我的觀察,李先菊大概50多歲,相貌丑陋(據村民講述早年不小心被開水燙過,右臉留有較為明顯的疤痕),身體虛弱多病,眼睛長期紅腫,衣衫襤褸。這些外部特征正好都符合當地村民對“蠱婆”的判斷,從人的意識和觀念中代表著“骯臟”。這種從個體外貌特征出發來確定“潔”或“不潔”的做法,直接導致了宗教文化學意義上的“潔凈與危險”二元對立。瑪麗?道格拉斯的研究表明,人類在不同領域有不同的分類系統,污穢(骯臟)就是不處于某種分類系統中(out of place)的東西。因此,在社會系統方面,污穢是對現有社會規范和社會秩序的背離,意味著危險,而危險本身就是超越了原有的分類體系和跨越不應該跨越的界限而造成的心理恐懼。對于污穢/危險的排除就意味著重返社會秩序,其手段包括禁忌、巫術儀式以及懲罰等。[6]194-196李先菊在外貌上的特征被視為“不潔”和“污穢”,這對于村民來說本身就意味著危險和恐懼,人為地將其區隔于社群之外,恰好暗含了社群試圖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努力,而區隔、解蠱的巫術儀式和不與之交往的禁忌則是嚴厲的懲罰手段。
以上大體是對李先菊“蠱婆”身份形成原因的分析。在大多數時候,一旦某個人符合上述三個因素中的任何一個因素,都很有可能被懷疑為“蠱婆”。“蠱”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事象,往往需要具備特定的文化基礎。“蠱婆”的產生同樣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正統文化和社會秩序對于“異”的排除(以儒家為基礎的傳統文化也不主張追求個性和獨立,而是遵循既有的傳統,大眾化才被認為是主流),因此如同李先菊這種在家庭和個體命運、經濟方面、外貌特征方面與主流的大眾文化存在較大差距的人比較容易被人懷疑為“蠱婆”,一旦被懷疑為“蠱婆”也就意味著被徹底排除到主流文化和社會秩序之外。在采訪李先菊的過程中,我也深深體會到了這一點:
(問:你平時和村里的人來往多嗎?)不怎么來往,我就一個人,平時也不用做什么人情,他們有什么事情一般也不會喊我。(問:你和先起來往多嗎?)也不多,一般有什么事情他還是叫我的,他平時也會給我送些吃的。(問:你平時靠什么活命?)我種點菜,拿到鎮上去賣,換點錢作為生活,其他時候也做點針線。(問:你現在身體情況怎么樣?)雖然時不時會得病,但總體上還是過得去,有時候害病了實在挺不過去了就會去鎮上診所打幾針、吃點藥。(問:你聽說過放蠱嗎?)聽說過,但我沒有見過。(此時李表現出了緊張的神情)(問:他們認為你會放蠱,你知道這事嗎?)我知道這事,但這個我也講不清楚,索性就算了,隨他們說去,我自己也反倒落了個自在,沒有這么多麻煩事。(問:大概什么時候開始知道的?)也就是前幾年,我搬回娘屋里沒過多久。
參見訪談錄音整理稿(編號2013071403)。
從話里行間,我們看到的是李先菊的無奈。她平時也不與人來往,過著孤獨寡居的生活,村民將其排除到了社會秩序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她的“蠱婆”身份是村民強加給她的,她本人并不具備放蠱的法術。這種強加的背后,恰好印證了我們之前關于“異”的分析,而這種人為的社會系統的排除,很重要的原因又在于她在家庭命運、經濟基礎以及外貌特征上的與眾不同。
三、巫蠱信仰及其社會功能
人類學家莊孔韶先生認為,巫術是指“企圖借助某種神秘的超自然力量,通過一定的儀式對預期目標施加影響或者加以控制的活動。”[7]364巫蠱屬于巫術文化之一種,也是通過借助于某種超自然力量,巫師或“蠱婆”以特定的咒語或儀式來控制蠱蟲,進而達到預期的目標。因此,從一定程度上來說,討論巫蠱信仰問題,也就是討論巫術信仰問題。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注意到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巫術信仰與之間的關系。
愛德華?伯內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以一種文化進化論的觀點討論巫術,認為“巫術是建立在聯想之上而以人類的智慧為基礎的一種能力,但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同樣也是以人類的愚鈍為基礎的一種能力。”[8]93這種觀點受到現代人類學研究的挑戰,因為巫術在科學技術已經飛速發展的今天仍然存在,而且承載著重要的文化信息。事實上,巫術與科學一樣,具有較高程度的相似性。弗雷澤認為,巫術與科學之間存在近親關系,兩者都認為“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規律的和肯定的。并且由于這些演變是由不變的規律所決定的,所以它們是可以準確地預見到和推算出來的。”同時,兩者在思維上也存在一定的相近性,都會運用到“相似律”和“接觸律”兩種思維模式,巫術中的這兩種思維發展成為“順勢巫術”(也稱之為“模擬巫術”)和“接觸巫術。”[9]15-17巫術、科學與宗教的區別就在于,“宗教認定世界是由那些其意志可以被說服、有意識的行為者加以引導的,就這一點來說,它就基本上是同巫術以及科學相對立的。巫術或科學都當然地認為,自然的進程不取決于個別人物的激情或任性,而是取決于機械進行著的不變的法則……因此,巫術斷定,一切具有人格的對象,無論是人或神,最終總是從屬于那些控制著一切的非人力量。任何人只要懂得用適當的儀式或咒語來巧妙地操縱這種力量,他就能夠繼續利用它。”[9]51-54這也就意味著,巫術信仰同樣追求對客觀規律的運用(非常接近于科學對規律的揭示),而不完全是一種主觀的臆測或者猜想,只不過對規律認識的前提假設可能存在誤差。巫術信仰承認并運用客觀規律的這種特點,也就決定了它對超自然力量進行控制的目標。巫術對自然環境的控制功能,在某種意義上極大地影響到人們對于巫術的信仰。在巫術成為社會普遍性信仰時,或者在某種特定的環境下巫術被個體選擇或認知時,巫術信仰在人的信仰體系中都會占據主導性地位。盡管弗雷澤曾樂觀地表示“巫術已染上了某些宗教的色彩或成分”,但是這并不能拉近巫術與宗教的關系,或許兩者僅有的共同點只不過都是以對超自然的信仰為前提(宗教關心的是人與神之事務,而巫術關心的主要是人之事務,不論其關注點如何,都信仰超自然力量)。
在人類學功能主義學派看來,任何社會事物或制度都會在特定的社會系統或社會結構中發揮重要功能。馬林諾夫斯基從“文化功能主義”進路出發,認為通過文化來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方式或行動就是文化的功能。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從“結構功能主義”出發,認為各種社會制度的功能就在于維系社會結構的正常運轉。如果上述理論成立,那么我們可以認定巫術也會具有某種社會功能,對社會個體的行為選擇和社會結構的運行起到某種作用。具體而言,巫術的這種社會功能首先表現在心理慰藉層面,隨后發展出社會整合功能。
關于巫術信仰在精神層面的鼓勵和慰藉作用,馬林諾夫斯基曾經作出經典闡述。馬氏在考察初民的巫術信仰后認為,巫術首先使原始人在心理上堅信某種力量的存在,在這種力量的幫助下會獲得成功,實現預期的目標;同時也會在精神層面上賦予原始人某種實用技術,在普通方法失效的時候進行調整。因此,“巫術就這樣使人進行最重要的業務而有信心,使人在困難情形之下而保持心理的平衡與完整――那就是沒有巫術的幫助,便會被失望與焦慮,恐怖和憤怒,無從達到目的的忍與莫可如何的仇等等弄得一蹶不振的情形。”[10]175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巫術信仰發揮著重要的心理功能,使原始人能夠從心理層面擺脫困難,避免社會文化的衰落與斷裂。埃文斯?普里查德對阿贊德人的田野研究表明,巫術對于阿贊德人的意義就在于,巫術能夠成為一種可以解釋不幸遭遇發生的自然哲學(用其他解釋方式可能無法做到這一點),因此阿贊德人只要遭遇到不幸就會在巫術那里尋找答案。[11]毋庸置疑的是,巫術心理激勵和精神慰藉作用的發生機制是心理暗示,通過某種特定的儀式或權威發生心理暗示作用。然而,由于本文討論的重點并不是巫術信仰的心理機制,而是巫術信仰及其社會功能。但是,此處關于巫術心理暗示機制的討論并不是多余的,而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巫術心理機制發生作用的必要條件――信仰,這也是后文進一步討論的基礎。
信仰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在東西方文化中關于信仰的討論可謂汗牛充棟,而且往往與宗教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有學者指出,“信仰是一種價值觀,而且一定是終極價值,是人通過內在的確定而表現的一種價值觀;信仰也是人類的一種精神現象,表現為一個人對一定觀念體系的信奉與遵從;信仰也是人的精神性基礎,意在解脫人們精神上的障礙,為實現人格的圓滿提供條件,是人類調節自身和環境關系的必要條件和手段。”[12]153這也就意味著,信仰呈現出一種層次感,既有神圣性又有世俗性。信仰的神圣性一方面使信仰無法在現實生活中到達,而只能通過信仰者的內心到達;另一方面使信仰觀念注入到信仰者的生活實踐中,作為信仰者的生活指引。盡管信仰的意義只有在生活實踐中才能得到體現,但是信仰神圣性的存在并不需要某種確定的儀式表現出來,而是存在于人的內心的確信;外在的儀式存在與否并不能作為判斷信仰本質的根本依據,只有確定性的來源以及信仰本身是否關涉人的生存意義才能作為判斷依據。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純粹的信仰首先表現出的是內心的確信,信仰是理性的升華也只是表明其關涉人的終極性意義,而不是證明其實踐意義。假如上述的討論成立的話,那么巫術所呈現的信仰本質同樣也是如此。巫術信仰同樣追尋的是人的內心的確信,巫術外在儀式與純粹的信仰本身并無太密切的關系,只不過是這種內心確信觀念在生活實踐中的自然衍生。一個純粹信仰巫術的人,并不會因為外部巫術儀式的固定或有無(抑或巫術儀式的表演)而影響到內心的確信,因為內心的確信已經轉變為一種更深層次的內心體悟,直接在現實生活中指引其行為。這一點在我對M鄉下關寨的巫蠱調查中也得到了印證,對李國斌母親的訪談如下:
(問:你當時是怎么知道你兒子中蠱了的?)他那天上午從地里干完活回來后肚子就絞痛,躺在床上打滾,頭天晚上和上午干活的時候還蠻好的。看到他這個樣子,病來得比較突然,我就懷疑他中蠱了。于是我就按照老輩人說的,拿來生黃豆給他吃,他也吃得津津有味。這個時候我就更加確定了。(問:你見過草鬼婆放蠱嗎?)我沒有親眼見過,都是聽別人說起過的,有人見到過草鬼婆給人放蠱,把粉末放在指甲里彈到喝的水里,還有的人見過草鬼婆斗法。(問:既然你沒有見過,你怎么這么肯定呢?)我們寨里從到“癟古”(意思是時間比較長)都有草鬼婆放蠱,雖然沒親眼見到過,但這個肯定是錯不了的。而且也有判斷中蠱和解蠱的方法,如果草鬼婆不放蠱,又哪里會有這個解蠱的方法呢。寨里人也都時刻防備著草鬼婆。參見訪談錄音整理稿(編號2013071405)。
從上述訪談記錄來看,李母以及村民對于巫蠱的存在是內心確信的,而且自覺地將其外化為自身的行為,如李國斌出現身體不適后被認定為中蠱,而不是去醫院進行診斷;再如,通過吃生黃豆來檢驗是否已經“中蠱”;又如村民平時避免與“蠱婆”的交往,等等。放蠱本身并無明確的儀式,而解蠱也并不具有固定的儀式,但這都不會影響到村民對巫蠱存在的確信,以至于人們在內心的指引下遵循特定的禁忌。對巫蠱的信仰,本質上來說是內心對善惡終極意義的追求,村民們認定“蠱”為“惡”的事物,“蠱”的存在也恰好滿足了文化中排斥“惡”的心理,試圖從心理上尋求一種關乎“善與惡”“潔凈與污穢”的平衡機制。這種平衡機制正好體現在巫蠱的社會整合功能方面。
從內心的確信出發,巫蠱建構出一種關于“善與惡”“潔凈與污穢”的平衡機制,不僅滿足了心理上的需求,而且還滿足了社會整合的需要。拉德克利夫―布朗認為,巫術通過反復地向人們灌輸那些對于完成重大任務和承擔不可推卸的重任,使之內在化價值、思想情感和態度,從而維系了社會的結構。[13]120-139這正是巫術所承擔的雙重功能,不僅在滿足了個體完成重任和克服困難的需要,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維系了社會結構的穩定。巫術信仰基于內心的確信,在社會成員普遍認同巫術以及巫術信仰的基礎之上為社會成員提供共同的行為指南,潛在地指引著人們的行為。除此之外,巫蠱的社會整合功能還表現在社會控制方面。比特麗斯?懷庭(Beatrice Whiting)認為,巫術作為一種社會控制機制,其效果是十分明顯的,而且社會越是缺乏法制或懲罰措施,巫術所表現出的社會控制作用越是明顯。[14]51-52盡管比特麗斯?懷庭討論的對象是法律不夠發達的初民社會,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是,即使是現代法律所涉及的地區,巫術也同樣發揮著這種社會控制功能,只不過是效果的強弱微顯的問題。本文所討論的巫蠱案件發生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該地地處湘西,群山環繞,交通不便,即使在社會快速發展的今天,仍然也相對閉塞。在這種條件之下,盡管國家多次開展“送法下鄉”活動,但進行社會整合的手段并不僅僅只有法律,更多的時候是由諸如習慣法、巫術規則等“小傳統”承擔著社會整合和社會控制功能。例如,在本文開頭講述的“鄰里糾紛案”中,李先起在庭審過程中所提到的“李先菊放蠱”一語,正是巫術對社會整合的具體表現。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巫蠱已經被村民視為進行“私力救濟”的重要方式。在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同樣也存在這樣的情形。例如,云南拉祜族以放蠱的方式來進行復仇或報復,他們通過模擬仇人來制作小人,并對小人某個身體部位施放蠱,通過念咒語的方式指示蠱蟲對小人進行吞咬,以為會使仇人的身體出現嚴重的疾病。[15]拉祜族的這種巫術信仰同樣是作為“私力救濟”的方式存在,而這種對巫術功能的確信恰恰為社會成員的不滿提供了宣泄的渠道,有利于社會結構的穩定。
四、作為“另類規范”的巫術規則與社會秩序
巫術信仰作為一種內心的確信,在現實中表現出心理平衡和社會整合兩個方面的功能。然而,這只是從宏觀層面對巫術功能的探討,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巫術是如何在實踐層面發揮社會功能的?結構功能主義可能并不關心實踐層面的功能問題,而只是將巫術置入社會系統或社會結構中與其他社會子系統進行比較,從而概括出巫術的基本功能。本文后續的努力將從具體實踐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闡述,分析巫術在實踐中的運作機制。
巫術在實踐中的運作機制主要是通過巫術規則展開的,這可能是一種“另類規范”。
張永和教授在對賭咒(詛咒)、發誓進行系統研究后提出“另類規范”的概念,認為“另類規范就是存在于某一個共同體中,能夠有效調整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關系,但是在國家層面上并不得到認同的那些規范……但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它們在社會中起到的作用實際上并不亞于主流的法律規范,實際上起到了主流規范的作用。”[12]14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張永和教授只是將“另類規范”限定為“賭咒(詛咒)、發誓”兩種典型的形式,而在討論巫術規則時并未將其納入到“另類規范”的范疇。在與張永和教授的一次學術交流中,筆者就此問題進行請教,問是不是可以擴大“另類規范”的范圍,將巫術規則納入其中,否則概念本身的周延性問題可能值得推敲。張永和教授對此并未明確表態,認為巫術規則更多的只是一種心理層面,而且大多數情況下表現為具體的巫術儀式;而“賭咒(詛咒)、發誓”并不需要特定的儀式。筆者并不贊同這一說法,而是認為巫術規則也應該屬于“另類規范”。事實上,在筆者看來,假如依照作者對“另類規范”的界定,巫術規則不僅可以視為一種“另類規范”,而且是一種極為重要的“另類規范”。
首先,本文所提到的巫術規則主要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在巫術信仰體系中人們關于巫術的內心確信;二是在現實實踐中關于巫術施放、感染、懲罰、禁忌以及禳解等一整套的規則體系。這兩個層面是密不可分的,第一個層面是第二層面的前提,只有對巫術的內心確信才可能存在有效的巫術規則;第二個層面是第一個層面的實踐表現,主要包括巫術的具體實施方式。從田野調查的情況來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M鄉下關寨的巫蠱規則也體現了這兩個層面的內容。從前文的討論可以看出,當地村民首先對巫蠱表現出了內心的確信,這是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一套觀念體系,無需外部證明的。此外,在巫蠱的具體實踐上,存在著“不與蠱婆接觸”“不吃蠱婆饋贈的食物”的禁忌,對于“蠱婆”放蠱的方式、蠱的種類、中蠱之后的表現、判斷是否中蠱的方法、仙娘的解蠱方式、藥師的解蠱方式等都有一整套的規則體系,人在中蠱之后都會根據這種特定的巫蠱體系進行處理。值得一提的是,巫蠱規則體系所表現出的懲罰規則,是其中重要的規則。
其次,巫術規則對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調整作用,這也是判斷巫術規則是否屬于“另類規范”的重要依據。作為一種類似于法律、宗教的社會規范,“另類規范”同樣對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起到重要的調整作用。例如,本文所提到巫蠱就體現出了對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調整。村民認為,“蠱婆”放蠱在一些時候是為了報復,這實際上是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反映。再如,村民對“蠱婆”的人為隔離和疏遠,以及“蠱婆”被人懷疑后自我放逐,這實際上反映了社會群體的劃分以及集體認同的增強,從一個側面體現出人與社會的關系。或許,對“蠱婆”的排斥正好增強了群體的認同與經濟合作,以競爭淘汰的方式將“異類”剔除,為社會群體的正常流動提供了有效機制,加強了社會的有機團結與合作。
再次,巫術規則在國家層面上并不得到認同。盡管人類社會產生巫術已經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在國家產生之后,巫術一直被視為某種危險而存在。在歷代成文法典之中,巫術、犯罪都有專門的罪名,而且一般處刑較重。《禮記?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 《三國志?魏志》云:“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 隋唐以后,巫術和犯罪逐步發展出造畜蠱毒罪、造厭魅及造符書咒詛罪、妖書妖言罪、偽造經文罪、師巫邪術罪等罪名。從這里可以看出,國家權力一直對巫術持有警惕或鎮壓的態度,國家極少對其認同,大多數時候是遵循儒家正統觀念。因此,如果說賭咒(詛咒)、發誓不為國家層面認同,那么巫術則更是如此,不僅不被認同,而且受到打壓。孔飛力關于清中葉“叫魂案”的研究同樣可以說明這一點,興起于江南席卷全國的“叫魂”案的確引起了弘歷的恐慌,盡管這種恐慌還來自帝國通訊系統的效率方面。[16]對巫術的警惕及控制是一個統治者不得不重視的問題。
最后,巫術規則在實際中起到了主流規范的作用。前文已經提到,巫術具有社會整合和社會控制的功能。在地方“小傳統”之中,巫術規則不僅是人們進行“私力救濟”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準則或指南。國家法律所具有的普遍性在進入到地方時必然會與“小傳統”產生沖突,甚至會受到“小傳統”的抵制。因此,在巫術盛行的社會之中,國家法律往往是蒼白無力的,巫術規則此時可能會發揮主流規范作用。例如,李先起在庭審過程中提到李先菊后,李永輝很快做出了讓步,原本分歧較大的案件很快也就達成了共識。再如,李母在村里用刀剁砧板無效之后,又請來“仙娘”為李國斌治療,就是不將其送入象征著文明與科學的醫院。無論是李先起、李永輝抑或李母,實際上都是在巫蠱規則的指引下作出具體的行為,巫蠱規則此時完全取代了象征著文明與秩序的法律。
從以上四個方面來判斷,巫術規則應該也是屬于“另類規范”。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另類規范”并不是一個封閉性的概念,而應該是開放性的。本文無法通過列舉的方式對“另類規范”的種類進行一一陳述,但是這足以提醒研究者們在對待這一概念的時候應該采取一種審慎的態度,必須要從上述四個方面區分某類社會規范是否屬于“另類規范”。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文的努力不妨視為對“另類規范”研究的進一步拓展或深化。正是由于巫蠱規則作為“另類規范”所具有的規范特性,它對于地方秩序的形成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正如“賭咒(詛咒)、發誓”對于秩序形成的作用一樣。
韋伯在法律社會學研究中對人們解決糾紛時訴諸于巫術、神諭、先知及儀式的現象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巫術之滲入所有的紛爭解決與所有的新規范的創造,結果是所有原始的法律程序皆典型帶有嚴格的形式性格。因為唯有當問題是以形式正確的方式提出,巫術手段才能夠給予正確的答案。而且,對或錯的問題并不能聽憑任意選取的巫術手段來解決,而是不同種類的法律問題各有其獨特的手段……訴諸神諭來裁決訴訟的原始方法,即使在其他方面皆高度理性化的政治―社會情境里,亦歷歷可見,例如埃及(阿蒙神的神諭)與巴比倫…
…法先知的支配恐怕是個相當普遍的現象。祭司的力量在各處極大部分是基于其作為神諭的頒布者或神判程序的主持者的機能;因此,當復仇越來越賦予為贖罪及(最后)訴訟程序所取代而治安得以漸次強化時,他們的權勢也往往如日中天。”[17]156,171韋伯的這段表述充分說明了巫術規則、法先知支配、祭司神諭等對于初民社會糾紛解決以及秩序形成的重要意義,盡管他認為巫術規則具備形式性,但他否認上述規范在具體運作中的理性品格。從韋伯之后的人類學家們的研究成果來看,韋伯關于巫術規則的形式非理性判斷可能需要再度審視。有學者通過研究韋伯的“英國法問題”
從韋伯社會理論出發,以判例法為傳統的英國法并不符合任何一種法律類型(如形式理性法),由此也就導致了韋伯社會理論在解釋“英國法”問題時所面臨的困境。這也表明了韋伯關于法律類型劃分的“理想類型”(idea type)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在解釋初民社會的規范與秩序問題時同樣存在。關于英國法問題的討論可參見李猛除魔的世界與禁欲者的守護神:韋伯社會理論中的“英國法”問題[A]//李猛韋伯:法律與價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11―241;李紅海普通法的歷史解讀――從梅特蘭開始[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347;魏建國韋伯“英國法悖論”的理性觀反思[J]求是學刊,2010(3),等等。,
認為韋伯所論及理性概念應該做適當的擴充,除了形式理性之外,還應包括實踐理性。
因此,初民社會同樣存在理性,只不過這種理性可能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實踐理性(如在實際中對社區秩序的維持),而不是形式理性。晚近美國學者羅伯特?C?埃里克森關于美國加州北部夏斯塔縣的田野研究同樣表明,“關系緊密之群體內的成員們開發并保持了一些規范,其內容在于使成員們在相互之間的日常事務中獲取的總體福利得以最大化。”[1]204這些自覺開發的非正式規范產生于實踐之中,在長期的合作與互動之中形成,對當地社會秩序的維持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所討論的巫術規則等“另類規范”對于社會秩序的形成同樣如此。首先,巫術規則等“另類規范”存在于“小傳統”之中,屬于“地方性知識”[19],是全體社會成員在交往中自覺開發出來的規范形式,在實踐中被社會成員普遍遵守。
其次,巫術規則等“另類規范”承載著巫術的社會整合和社會控制功能。前文已經討論巫術的社會功能,社會成員在解決糾紛的過程中可能會運用巫術規則,而且巫術規則運用的基礎是社會成員對巫術的內心確信。例如,在權利受到侵害的場合下,受害人可能會運用巫術尋求一種“私力救濟”或者雙方在進行賭咒(詛咒)、發誓之后進行和解,這對于社會關系的恢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再如,本文所討論的“放蠱”以及一整套“解蠱”方法實際上都是權利救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最后,“另類規范”包括巫術規則、賭咒、發誓等非正式的規范,這些規范與法律規范一樣都對社會成員的權利和義務進行區分(只不過這種權利義務內容是通過另一套話語體系表現出來),社會成員在交往及規則運用的過程中會遵循權利義務體系,調整著社會關系,這促使了社會秩序的形成。因此,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巫術規則等“另類規范”形式在實踐中發揮著社會整合和社會控制功能,與法律、宗教、習慣法等社會規范一起共同維系著社會秩序。
五、結論
巫術作為一個重要的問題,一直未引起法律人類學研究者們足夠的重視。本文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M鄉下關寨的“中蠱”事件出發,深入挖掘巫術背后的運行機制。這種努力或許是失敗的,但也有可能為后續關于巫術的研究提供比較的樣本。概而言之,本文試圖得出以下四個方面的結論。
第一,巫蠱傳統符合人類排除“異類”的社會心理。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群體之中,對于不符合普通大眾審美或經濟水平的個體,都會被劃定為社會“異類”,在人際交往網絡之中排除出去。威廉?富特?懷特對意大利人貧民窟(被稱之為“科納維爾”的波士頓北區)的研究表明,由社會閑散青年組成的“街頭幫”一直被社會主流文化視為“異類”,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成熟的非正式組織和規則,“街頭幫”成員都以之為行動的準則。[20]從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蠱婆”身份的形成正是社會排異心理作用的結果。“蠱婆”由于家庭命運、經濟條件以及外貌長相等方面的差異,無法與其他社會成員進行正常的交往,因此主流文化對其并不認可,最終將其予以排除。另一方面,一個社會如果要正常運作必須具備對“異類”的排除機制,否則就不利于對主流文化的保護,巫蠱文化中“蠱婆”身份的形成正好滿足了這方面的要求。
第二,巫蠱信仰是一種內心的確信。這種內心的確信是無需證明的,只要社會成員在內心對其認可即可,這也就為巫蠱社會功能的發揮提供了心理基礎。巫蠱的社會整合和社會控制功能的確是以內心確信為前提的,在此基礎上才能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我知道,你知道”正好表明了社會成員之間對于巫蠱的內心確信,此時巫蠱規則成為社會成員共同的行動指引。因此,正是從內心的確信出發,巫蠱建構出一套關于“善與惡”“潔凈與污穢”的平衡機制,不僅滿足了心理上的需求,而且還滿足了社會整合的需要。
第三,巫蠱具有社會整合和社會控制功能。人類學功能主義學派認為,巫蠱與法律、宗教等社會子系統一樣,在整個社會系統中發揮著重要的功能,各種社會子系統共同維系著社會結構(如前文所提到的巫蠱的“私力救濟”功能)。法律與巫術可能共同存在于一個社會之中,即便是法律文明已經普及的地區,巫術也仍然存在,并且發揮著自身的社會整合功能。兩者之間的關系可能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也就是說,在法律較為落后的地區,巫術可能占據主導地位;而在法律較為先進的地區,巫術則很有可能居于次要地位,但這絕不意味著徹底消失。因此,巫蠱的社會整合和社會控制功能即使在今天也同樣存在,尤其是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偏遠的山區,巫蠱的這種功能可能更為明顯。
第四,巫術規則屬于“另類規范”。首先巫術規則主要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在巫術信仰體系中人們關于巫術的內心確信;二是在現實實踐中關于巫術施放、感染、懲罰、禁忌以及禳解等一整套的規則體系。其次,巫術規則符合“另類規范”的基本特征。巫術規則不僅調整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關系,而且大多沒有被國家層面認可,卻在實際中起到了主流規范的作用。最后,作為“另類規范”的巫術規則在實際中維持了地方“小傳統”中的社會秩序,也為巫術社會整合和社會控制功能的發揮提供了具體可行的實踐規則。從人類學田野研究來看,巫術規則實際上是一種實踐理性,它與其他“另類規范”一樣都屬于“地方性知識”,“另類規范”對于社會秩序的形成與維持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行文至此,我們大致可以回答本文開篇所提出的問題。庭審過程中,在李先起提到李先菊之后,雙方由分歧較大很快達成共識,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李先菊“蠱婆”身份所帶來的震懾力,這種力量的根源正是巫蠱文化以及社會成員對巫蠱的內心確信所賦予的。而李先起的“你等著,我讓先菊放蠱給你家,讓你全家死絕”一語正是通過巫蠱進行“私力救濟”的重要表現形式,也是巫蠱調整社會秩序的重要體現,而且在現實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正是在雙方共同的巫蠱信仰基礎上,李先起與李永輝之間的鄰里糾紛案發生逆轉,雙方很快達成調解協議,此時法律面臨著一個“尷尬的退場”,這或許是法教義學者們始料未及的。
因此,在面對具體法律現象時,法教義學與社科法學應該采取一種合作互補的態度,前者可能是基礎性的,而后者則可能是超越性的,特別是后者所采取的研究進路能夠為我們當下理解和闡釋一些法律現象提供一種較為合理的視角。
參考文獻:
[1]李瑤巫蠱方術之禍[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5
[2]洪涵巫蠱信仰與社會控制[J]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9(5)
[3]陸群湘西巫蠱[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4][英]馬林諾夫斯基原始人的犯罪與習俗[M]原江,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5]閻云翔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M]李放春,劉瑜,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英]瑪麗?道格拉斯潔凈與危險[M]黃劍波,盧忱,柳博S,譯張海洋,校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7]莊孔韶人類學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8][英]愛德華?泰勒原始宗教:神話、哲學、宗教、語言、藝術和習俗發展之研究[M]連樹聲,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9][英]J G 弗雷澤金枝:上[M]徐育新,汪培基,張澤石,譯劉魁立,校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10][英]馬林諾夫斯基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M]李安宅,譯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
[11][英]E E埃文斯?普里查德阿贊德人的巫術、神諭和魔法[M]覃俐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12]張永和信仰與權威――詛咒(賭咒)、發誓與法律之比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3][英]AR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會的結構與功能[M]潘蛟,等,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
[14]周蔚,徐克謙人類文化啟示錄[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15]楊洪,張靈鈺淺談拉祜族的巫術信仰[J]思茅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6)
[16][美]孔飛力叫魂:1768年的中國妖術大恐慌[M]陳兼,劉昶,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
[17][德]韋伯法律社會學[M]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18][美]羅伯特?C?埃里克森無需法律的秩序――鄰人是如何解決糾紛[M]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